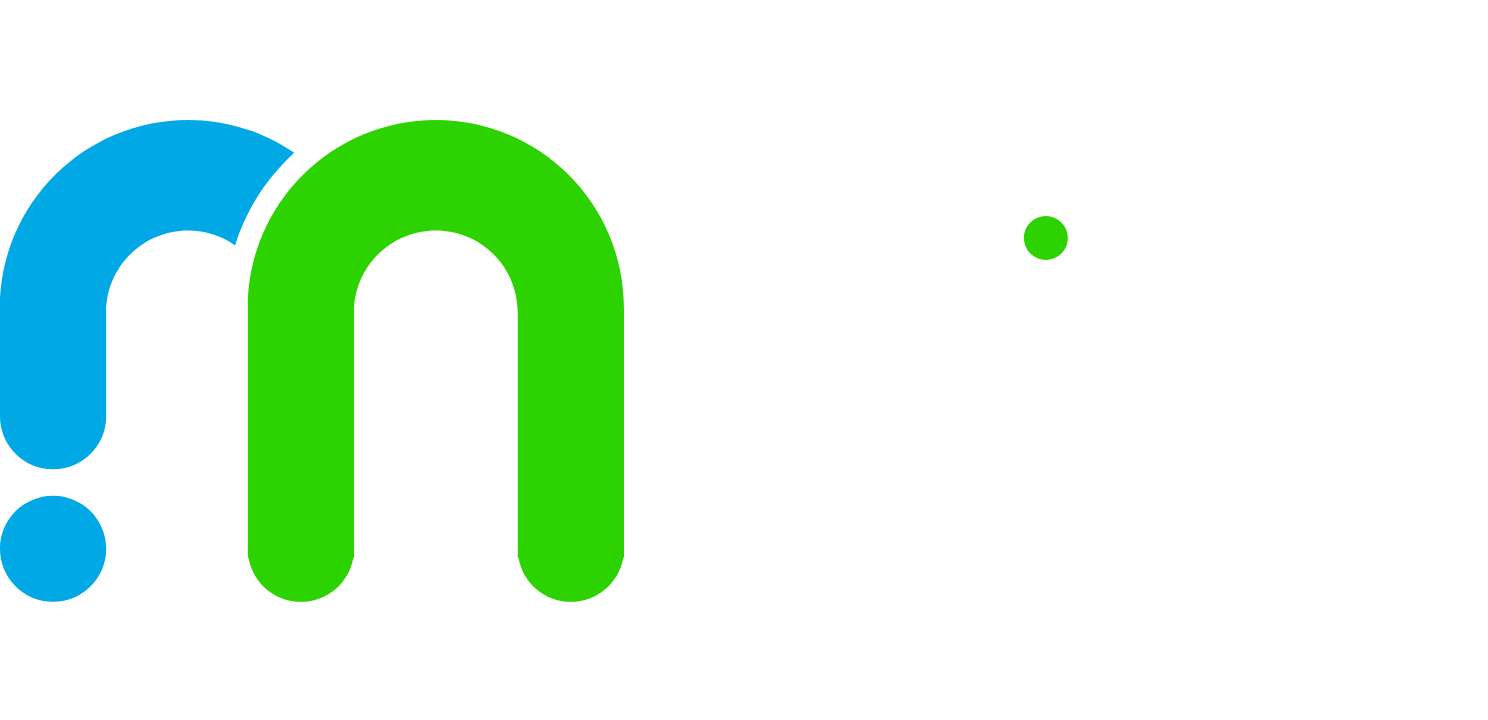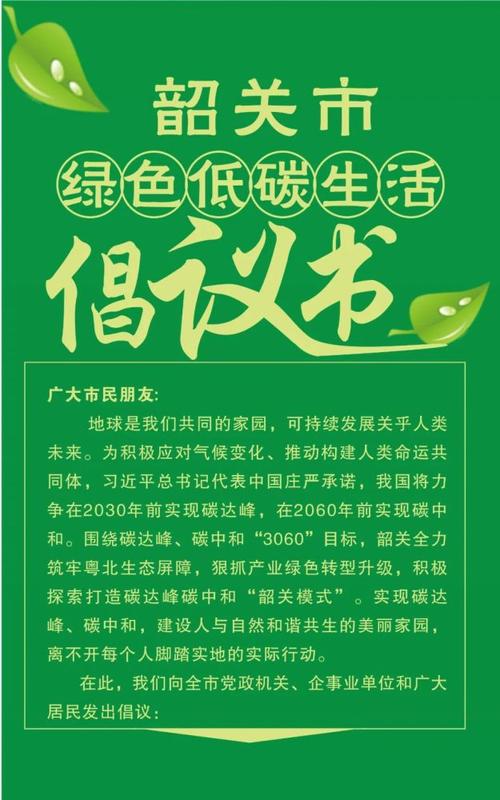江门的龙舟水在端午后逐渐谢了,代之以烈日似火。假如命运运限好,正午会下一阵过云雨降降温。这时,饭点赶饭堂的人则会说:“阴公咯,专淋打工人。”
雨后的天空经常一碧如洗,飘着几缕蝉翼似的云,整个下昼晴朗得无可阻拦。

(蓬江区文广旅体局 朱婉姬 拍摄)
于是盛夏的午后,江门年夜年夜小小的咖啡馆逐步多起了人气,门外空调的外挂机隆隆地宣泄暑热。李光耀说:空调拯救了新加坡。这话也是讲给江门听的。
蓬江区建设路的三轮车咖啡馆老是座无虚席。
这家咖啡馆的开创人从前推着三轮车在帝王酒吧门前卖咖啡,以低廉的价钱和快速的出品,从凌晨劳作到黄昏,方便了环市街道以咖啡提神的上班族,积聚了年夜量的人气。后来帝王酒吧爽性把前厅租给他,用作门店。从此勤劳的咖啡师离别了日晒雨淋。
(图片起源于收集,已获作者授权)
大概是受够了暑热,三轮车咖啡店的装饰极其清新:银白的墙面、水鸭色的坐垫,深蓝米白相间的马赛克地砖,配上两台呼呼的中间空调,这间十余平米的小屋就像一艘赤道热流中的潜艇,自顾自地清冷。
店内的咖啡客围着吧台而坐,打游戏,玩塔罗牌,抱着电脑赶营业;多是邻近的青年,与其说熟客,不如说是邻里,乃至把家用杯子拿来,挂在后墙。吧台内繁忙的两位咖啡师,一边嘴不绝地介入客人的话题:家庭、恋爱、沐日,一边调饮品,像屋主接待亲友石友,言笑晏晏,似乎与生意无关。
(图片起源于收集,已获作者授权)
有位咖啡师,江门开平人,零零后,只身在蓬江营生,见这里五点放工,就来了;为人忸怩、勤快,余暇时宁静地抱起收养的小猫,摇着臂弯,像哄一个婴儿。我说,你不盯着场子,不怕有人逃单吗。
“那他只能逃一两次,久了我们会发现的。那一两次就当宴客吧。”
豆青色的格子窗外,透过人行道上细叶榕的疏隙,下昼的阳光抹上了马路对面、光亮眼镜店的伟大告白牌。骄阳带来的炎热变得悠远,徒留豁亮,窗外的叶子通透得像翡翠。青年们在绿意盎然里演绎故事。
一日,某醉汉摇摇晃晃撞上了店外的榕树,晕乎乎地呆坐在行人性上,警员来了,医护职员来了,中暑似的他含混其辞地说:“渴,渴,颈渴……”三轮车内,一位蜜斯姐闻声送去了水。喝了一半,彷佛醒了,撅着嘴说:“要喝咖啡。”蜜斯姐扬起了笑意,递给他一杯浓浓的冰美式。剧场包厢一样平常的咖啡店刹时充斥了欢快的空气。
有位同伙,蓬江人,家住东边的白石,喜好舞蹈和音乐。周六下昼常在金山年夜厦的芭蕾跳舞中心训练,停止后,和队友们声势赫赫地下楼,到三轮车点一杯冰咖啡,纳凉,然后背靠阳光,追着影子回家,像许多年前下学那样。她小时刻感到很平凡,如今感到很快活。
有个须眉,家在蓬江建设路,单元在恩平,每个周日的下昼,老是携妻到三轮车,点两杯摩卡,缠绵消磨,然后独自开车去单元。摩卡是甜的,换作拿铁、美式,则过于苦涩了。三轮车的下昼韶光本就短暂,周末欢聚的进度条即将耗完,在迫近告别的韶光里,酸苦味道越尝越伤怀,不如来一口摩卡吧。眷恋的甜美蓦然而生,萦绕整个征途,似乎斜阳也为蜜意而订制,与西沉无关。
(蓬江区文广旅体局 朱婉姬 拍摄)
五点一刻,三轮车打烊,青年们相互作别、祝安全,就像聚首散场一样。咖啡师们用杈竿撑起了格子窗,布粉器和粉锤敲下的咖啡残渣溢出浓香,飘到店外;扫除窗台扬起的咖啡粉在榕树下斑驳的日光里翩跹,引来行人的驻足。日光下移,在建设路和环市路接壤的联排石米楼顶徜徉。那是90年月的旧楼,托着太阳把长街染成了金黄。
梁远航 拍摄
下昼的阳光,灿烂而迟慢,带着白日将逝的迷恋,像一日之中的秋日,最能承载回忆。于是,姜文拍摄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纪念童年:胡同、筒子楼、白杨叶的沙沙声,尽在金黄的斜晖里。
侯孝贤的《童年旧事》,榻榻米、芭乐树,下昼的阳光织入了天井,操着闽南语的白叟,欲说还休。
多年后,三轮车的青年,回忆蓬江的炎天,年夜概少不了石米楼、细叶榕,和阳光里纷飞的咖啡粉。
编纂 | 蓬江宣布编纂部
起源 | 作者/陈念新